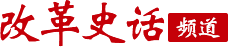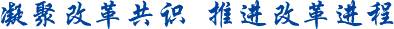北朝文学的自然书写
发稿时间:2019-09-18 14:34: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席格
北朝文学中有丰富的关于自然审美的书写,但受制于文学史观念、美学理论史范式等因素,现有的中国美学通史、魏晋南北朝断代美学史著作,并没有给予这些书写以充分关注。因此,有必要揭示北朝文学关于自然审美书写的具体内容,从而彰显其美学价值。
《水经注》与山水审美
宗白华曾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郦道元的写景文属于“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的作品,高度肯定《水经注》在山水审美书写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在现有书写范式中,哲学理论品格不足的《水经注》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美学理论史的叙述视野。而实际上,《水经注》的山水写景文章蕴含了丰富的审美观念。
在郦道元笔下,山水已不再是基于宗教性崇拜的“神性”山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山水,也不是南朝受玄学影响的“玄言”山水,而主要是回归自然山水本身的“畅神”山水。郦道元书写自然山水的方式可分为“身游”和“神游”两种。所谓“身游”,指作者在实地考察水道过程中,对亲身游览体验的书写。如他在《水经注·巨洋水注》中记载与友人在巨洋水边游玩休憩:“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笋,匪直芳齐芍药,实亦洁并飞鳞。”而“神游”则指作者不能实地考察,只能基于史地、诗赋、志怪、谶纬、书简等资料,发挥审美想象书写山水。如他描写长江三峡之巫峡的写景美文,便是根据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稍加改动而成。
郦道元所描绘的山水景观类型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山水景观,即山水本身展现出纯粹的自然美。此类山水既不是人伦道德的象征,也不是长生成仙的媒介,而是天然的山水。这类描写有“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望之极为奇观”的瀑布,有“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的潭水,还有“四面壁绝,极能灵举,远望亭亭,状若单楹插霄”的山峰,等等。郦道元不仅以文学笔触描绘山水之自然美,还认为山水之美有“画”的品格。他在描写教水时说:“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赪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望若图绣”,实则是以艺术性眼光审视山水,与西方审美范畴“如画”具有一定相通之处。
另一种是人文山水景观,指文化与自然山水交融所形成的景观,如岩画、石窟、碑刻、建筑、诗文及神话传说等景观赋予山水以人文性特质,从而呈现出历史感、神圣感等特性。以郦道元对晋水的一段注释为例:“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这段文字简明扼要地交代了晋水的发源地,并由“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指出沼泽的由来,接着便对沼泽的人文景观进行描述。沼泽西边依山傍水,有唐叔虞祠和凉堂,水上有飞梁,并且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亲朋好友、士人等结伴游乐的“胜处”。
可以说,郦道元寻山访水,既是考察自然地理的过程,又是山水审美体验的过程。由此,他不仅撰写了代表北朝文学成就的写景文,而且结合切身的山水审美体验,提出了“望若图绣”“取畅林木”“物我无违”与“神心妙远”等重要审美观念。这便赋予《水经注》以重要的美学价值。
乐府民歌与草原审美
与基于农耕生产生存方式的山水田园审美不同,草原审美由游牧生产生存方式孕育而成。自晋室南迁后,北方草原审美文化便注入中原文化,草原民歌也传入中原及江南地区。但由于语言限制,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即便如此,通过《敕勒歌》《折杨柳歌辞》(五曲)、《折杨柳枝歌》(四曲)与《企喻歌》(四曲)等,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北朝时期的草原审美风貌。
《敕勒歌》通过脍炙人口的语言,既描绘了北方草原苍莽辽阔的风景和游牧民族自由奔放、与草原自然环境相融为一的生存状态,又展现了他们在宇宙时空认知方面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差异。再以《折杨柳歌辞》中的一首为例:“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郭茂倩《乐府诗集》)歌辞生动描绘草原牧马的壮美景观:水草丰美的无垠草原上,骑技高超的牧马人骑着健壮的骏马自由驰骋,一边放牧,一边赛马。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移生活中,积淀生成的刚健、勇敢、自由、豪放的审美精神跃然而出。
与《敕勒歌》《折杨柳枝歌》等北朝民歌包孕的自由奔放、乐观昂扬等审美精神不同,草原审美在中原或江南地区诗人的诗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貌。一方面,这些诗人来到草原后,难以获得与游牧民族相似的审美体验。典型代表是江南诗人王褒、庾信到北方生活之后,游牧民族所乐道的草原地区在他们笔下变成苦寒之地。再如,作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牧马,在董绍的《高平牧马诗》中却充满悲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正是对草原审美文化的深层体验,促成王褒、庾信等文学审美风格的转变。如杜甫所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便与庾信在北周时期对草原审美文化、审美精神的体验与感受密切相关。此外,这种南北差异也为从文学维度考察草原审美精神对中华审美精神生成的贡献,提供了有力佐证。
“望海诗”与海洋审美
海洋作为自然审美的内容,在中国文学艺术中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但到了两汉魏晋时期,随着浑天说、宣夜说等宇宙认知的兴起,以水系为中心的地理空间建构愈发受到重视,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封闭性空间认知之外,出现了基于水系、朝向大海的开放性空间认知。在文学创作上海洋审美书写持续出现,如班彪的《览海赋》、曹操的《观沧海》、王粲的《游海赋》、庾阐的《海赋》、孙绰的《望海赋》、谢灵运的《游赤石进帆海诗》、张融的《海赋》等。这些作品虽然并非全都基于实际的海洋生存经验书写而成,且主要以观、望、览、睹等方式获得审美体验,有些甚至具有浓郁的游仙风格,但从中仍可看到海洋是北朝文学自然审美书写的有机构成部分。
北朝文学关于海洋的书写,尽管在作品数量、整体成就方面不如南朝,但仍有一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例如,郑道昭的《登云峰山观海岛诗》延续了游仙题材,虽运用想象描绘神仙与仙境,但开头“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一句,却真实书写了诗人对大海风景的眺望。祖珽的《望海诗》“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沿用“望”这一审美静观的模式,直接描绘作者所见之波澜壮阔的海洋景观,且抒发诗人的感叹伤怀之情。钱志熙认为该诗“有比较开阔的意境和劲健的气骨”,“出色地描写大海的气象”,“唐人造句之工者,不能过之”(《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可谓评价极高。
北朝的海洋审美书写从游仙向写景抒情过渡,既有当时哲学观念转变作为基础,又有现实审美革新的动因。如据《魏书·高宗纪》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在太安四年(458)登临碣石山:“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拓跋濬到碣石山并非是为寻仙求药,而是以“观沧海”的“乐游”为目的。透过这则史料可看出,海洋审美在北朝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概言之,北朝文学的自然审美书写在山水田园、草原与海洋三大领域,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一方面,这些书写展现了北朝文学不同于南朝文学的特质,凸显了北朝文学自然审美书写的文学史价值;另一方面,这些书写也呈现出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北朝审美观念的多元融合特征,彰显出北朝文学审美书写在美学史上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