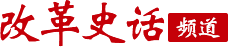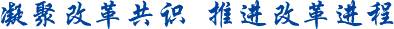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发稿时间:2018-03-02 11:11:5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忠炜
2017年10月,日本汉学家大庭脩的代表作《秦汉法制史研究》由徐世虹教授领衔重新翻译出版。此前,由林剑鸣教授于1991年主译的《秦汉法制史研究》曾使国内学界首次窥见此书全貌,对秦汉法制史、制度史乃至简牍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次,以“明确相关学术观点的表达”为宗旨的新译本,相信对准确理解大庭脩原书论述更有助益。
木简学之花:元康五年诏书册
新译本正文由五篇构成:第一篇为综论,是全书之纲;第二至五篇为全书之目,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文后有《后记》,叙述成书缘起。全书收录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最后补入的是在1981年,跨度几近30年。用30年的时间去磨砺一把“剑”,怎能不锋利?原著成就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不足为奇。与日文原著有所不同,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相关文章,在新译本中以“附录”的形式补入。
此书堪称体大思精,与其泛泛论其价值,倒不如以个案的形式,从不同层次加以认知。
以功次升迁的制度
基于对传世文献的熟稔,也基于对出土简牍的敏感,咀嚼《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之语,大庭脩提出了如此论断:“汉代存在着只要是长期任官工作,即使没有能力也可以获得晋升的制度”。他还指出,“劳以出勤天数为主,出勤状况是增减劳的依据,劳的多少表示官吏业绩的高下”,“汉代官吏的晋升多通过积劳功次”。用今天的话说,功劳更像是资历,功劳制度,近乎依据资历深浅决定升迁的制度。
大庭脩的这一“发明”之见,19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真切地被体会到。1995年,依据对居延新简“徐谭功将简”的分析,胡平生首次厘清功与劳之间的递进换算关系,提出“凡积四岁劳,即进为一功”的重要观点。这是推进功劳制研究的关键一步,尽管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结论。1993年出土、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尤其是其中“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首次印证了功劳制度在仕进史上的意义:根据廖伯源的统计,郡县属吏以功劳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县道长吏(县令长、丞、尉),在可供有效统计的数据中竟达40%之多,这是学界此前所不知的。
里耶秦简博物馆中有枚分栏书写的功劳残牍,第二栏中记载了某人的仕宦履历:“凡【十】五岁九月廿五日”,是其任职时间的累积计算;“【凡】功三”,则是功劳折算的结果——一功可抵四岁劳,获得最直接印证;“三岁九月廿五日”,是折算后剩余的劳日。对于这枚残牍的意义,笔者曾经写道:“在秦灭六国、实现统一的进程中,因军功入仕途、升迁固然是途径之一,但还存在着累日积劳的功劳制度。”今天,我们对秦汉功劳制的认识,已非1950年代所能比拟。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比大庭脩更加高明,只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
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绝大多数都是废弃的文书,是名副其实的“残篇断简”。国内学界多将之视为研究的辅助材料,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其意义,是多数学者的研究取向,也是简牍研究的主流范式。大庭脩关于“功劳制”的研究,从某种情况而言,也可以视为这种取向的产物。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在永田英正看来,尽管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简牍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有可以利用的部分,也有利用不了的部分,而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利用的部分在简牍中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简牍是无用之物。
认识到既往研究的局限,如何开启新局面,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日本第一代汉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有了“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并最终奠定了“日本汉简研究中最具特征且富于独创性的领域”。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是将简牍本身当作研究的主体,而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资料。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对资料本身进行客观细致的考察,探究材料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成为关键。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像是拼图:孤立地看,单个拼图的信息着实有限,若将它摆放到适当的位置,不仅可以发现它的功能,还可以发现各拼图间的联系,由此窥见全貌。
对于导入“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藤枝晃在《居延汉简研究·序》中曾以“剑法”为喻写道:挥着剑乱舞乱砍,即使真的能把敌人杀死,也很难称得上是正规的剑法,只有从基础开始按剑谱进行训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剑法。
作为居延汉简轮读会成员的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修习“剑法”的结果,各有成就:鲁惟一以复原汉简简册为中心,撰写欧美学界汉简研究的开山之作;永田以簿籍简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的“书式”为基准,并参照出土地点等信息,展开“集成”式的研究,开创了汉简研究中的“永田方式”或“永田流”;大庭脩主要对汉代制诏和令进行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最为学界称道的篇章之一。
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是大庭脩法制史、简牍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古文书学孕育之花。出土时的残篇断简,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形态即如此,是编绳朽断后顺序混乱的结果。简册复原,以笔迹相同、出土地相同、内容关联等为主要依据。1961年,依据上述原则,大庭脩发表了元康五年诏书册复原的成果,将散乱存在的8枚简牍恢复为一个整体。这是居延汉简中的第三份册书,也是被学界复原的第一份册书。这份被复原的册书,鲜活地揭示出行政命令是如何被提出的,经由什么样的程序颁行,又是如何依次被传达到基层社会,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简册复原虽具多方面的意义,笔者更钦佩大庭脩对汉代制诏的研究。
大庭脩根据汉代制诏的内容,将其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下达命令;二是官吏在委任权限内提出议案、并获得认可,然后作为皇帝命令公布;三是前两者形式的复合,亦即皇帝表达了政策指向,将具体立法委托给部分官吏。按,基于内容而分析形式,从古文书学的理论看,属于典型的“样式论”。经过此番分析,习以为常且乏味的公文书,被大庭脩发掘出前所未知的意义:汉代令的立法程序首次被厘清,时在1963年。
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修习剑法的目的,固然在意胜负,但又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体悟剑道。大庭脩所体悟的剑道,似乎可用“实事求是”概言之。其自道其之语是:“初学之际,社会上正盛行时代区分的争论,对此也感到兴奋,然而却不适应,对流行的经济史领域也不太感兴趣。如果要做,界限比较清楚的法制史似乎合乎我的性格。较之高迈的理论,还是地道的考证有意思。”明乎此,也就明白本书以考证或实证为特色的原因所在。
大庭脩对王杖简的关注,可能是最好的注脚。1975年,他发表了对王杖十简排序的新说,但很快就受到了学界批评。尽管心中仍有诸多疑问,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读罢滋贺对拙文的评论,坦率的想法是,滋贺的说法恐怕是稳妥的”。1986年,基于新见的王杖诏书令册,他修正、撤回了“有关决事比、谳的一般性的看法”。不过,他对王杖简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1995年发现王杖简的排序,并对所谓的“挈令”问题提出已见;1996年,发表以《汉墓出土的简牍——特针对王杖简牍》为题的论文,阐述处理墓葬简牍的方法。在21年内,持续关注同一主题,或是修正乃至撤回旧说,或是拓展既有论题,或是从方法层面进行探索,无一不是作者求真求是为学态度的体现。
在大致梳理王杖简的研究序列后,似乎有助于解开一个“谜团”:大庭脩很早就对睡虎地秦简给予关注,但却终究没有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出于何种考虑?译者推测是对竹简的编联依据存在疑问,这大概是可以信从的。在“津关令”的研究中,大庭脩也写道:“看到对最早的释读排列成果完全信赖的研究,从简牍研究的方法来说,不禁感到多少有些不妥。”对墓葬出土简牍性质的判定,成为解开“谜团”的又一线索,“简牍作为墓主冥界生活必需品之一而被有意随葬的”,那么,“如何看待它们的性质,关系到它们作为资料的使用价值,因此论者必须首先明确自己考察范畴的合理性。”这与学界通常将墓葬出土的简牍视为“真文书、真记录”的看法明显有别。
考证是依赖材料说话,但问题也由此而生:一方面是对既有材料的理解出现偏差而导致论说不确,一方面是不断出土的新见材料会纠正、补充或拓展既有的论断。对此,《代译者序》中已有指明,不赘。实际上,对于考证的局限性,大庭脩有清醒认知。修正、撤回王杖简的论说,“可以说是不逮所致,但这莫如说是无法预测将会有怎样的资料出土的中国史研究者的命运。”虽如此,考证或实学的传统,依然在被学者坚守。
当翻译作品几乎无法纳入“科研考核”的序列时,主译者却甘心付出10多年的时间不懈为之,且不为翻译或出版事宜申请任何资助或补贴。“非有对学术本身所抱持的热情不足以成其事”固然为其一端,更重要者在于师生道义之薪火相传,自不欲有一丝一毫的名利之念沾染其间。主译者“自度无愧于用心”一语,自当反复体味,尤其是此书出版正值大庭先生祭日将至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