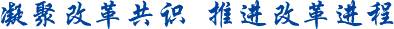日本为何对历史反省不彻底?
发稿时间:2013-08-12 00:00:00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邓聿文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68年周年纪念日,安倍内阁中的两位大臣已经公开表示该日要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最近也再出狂言,呼吁日本应效仿二战爆发前德国纳粹政府的做法,在谁都没注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修改宪法。
安倍内阁自去年12月26日组阁以来,已日益右倾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参院胜选后,更是挟民意而成为日本战后最右倾的内阁,使得邻国十分担忧。那么是什么造成日本在战后变得右倾色彩如此浓厚?笔者认为,在探寻其中原因时,有必要回到战后历史的起点,及整个冷战史,去看看当时情况。日本的右倾化并非是突然兴起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期。这一点,和同为战败国的德国相比,显得尤其明显。
二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而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一段时间。据统计,日本当时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3万余人。比起德军的疲惫状态来说,日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事实上,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军部围绕着主战与主和争执得很厉害,而军队在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刻,还在负隅顽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后因美苏“冷战”的发生,德国东西分裂的状态被固定下来。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后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的占领体制则不同,虽然是以盟国名义占领,实际上由美国单独占领,民族的单一性和国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后果是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感受没有德国人那样深刻;而占领结构的这种差别,也直接影响着两国战后的民主改革。
战后初期,出于彻底铲除法西斯势力和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的考虑,盟国对德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民主改革。对于德国来说,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从来没有成为国民的普遍意识,日本更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着重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物质主义,对于西方的民主思想不过是学了某些表象。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两国进行民主改革十分必要。但是,基于德、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以及盟国各自的利益,两国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击军国主义势力上有很大差别。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说,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有两条: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这就决定了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舆论也一直要求美国政府将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天皇制。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后因冷战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后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客观上等于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对日本国民而言,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
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终结。
概言之,战争的受损程度、盟国占领体制的差别,以及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导致日本没有认真地去清理这场战争和历史。
第二个因素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当然日本的这种倾向也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要求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美国政府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之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发言权,其突出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战后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学家们独立撰写,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个方面,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导致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分属“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相似。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这种等级观念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尊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这种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战争的失败说明他国“不守本份”,至多是说明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行不通。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也不必为发动战争而道歉。
“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善恶观模糊不清。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这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才有了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成为一般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从神还原为人,但对天皇的“忠”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战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严格区别,且根本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
最后,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性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
二战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日本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同德国战后对纳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非常不严肃,背离史实。许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指出,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历史课本中也通常回避这段历史。文部省还把“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删除有关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试验的段落,并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字样。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也一再得以通过官方审定。歪曲历史、掩盖民族的罪行,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后代,只会使后代对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更加轻率的态度,更无法培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取信于世的文明民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