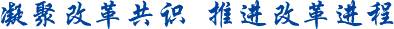监察官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发稿时间:2019-05-15 14:37:47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先昌
核心阅读
中国传统监察官制度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当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制定监察官法、全面实施《监察法》,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监察法》第14条规定:“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设置、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已将监察官法纳入其中。建立监察官制度,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的重要举措。监察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特色鲜明,而作为制度主体的监察官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孕育产生的。
监察,从词意上具有监视、监督、调查、纠举、督责等。早在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国家事务中,已开始出现监察因素和监察活动的某些萌芽。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官制中的小宰、宰夫,分别是在王宫和朝会上维持秩序和纠察大臣失礼行为的官员,而御史主掌记录君臣言行和全国的文书档案。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换的阶段,为解决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法家学派论证了确立监察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为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出谋划策。他们提出用法令和制度来规范官吏们的行为,以严厉的督责来净化官场风气等主张,被后代的秦汉统治者所采纳。惩治官吏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的监察制度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建立起来,其标志是监察机构——御史台(府)的建立和定型,长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名称的确立,以及地方监察法规《六条问事》的制定和实行。与此相适应,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也在此时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得到较快发展,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从九卿之一的少府中独立出来,监察官员名额、名称稳定,监察职权扩大,选拔监察官的标准制度化,监察体制由多元向单一制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善时期,隋代中央监察机关最具历史意义的变化是取消了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的一般监察职能,只有当“御史纠不当”时,尚书左仆射才可以反纠弹,这是制约御史权力的一种创新性措施,为唐宋等朝代继承沿用。唐代中央监察机关实行一台三院制,御史台下设台院、置侍御史,殿院、置殿中侍御史,察院、置监察御史,内部分工明确,职责权限清晰。监察与审判并重,司法功能强化,御史台狱应运而生。
宋仿唐制,实行一台三院制,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中丞,总判台事。“台官职在绳愆纠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
元代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台,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为三大府。元代御史台的地位要比前代高,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元代监察法规建设也取得较大的成就,监察台纲《宪台格例》内容已涉及监察机构的职能、监察权责、工作程序、监察纪律等方面。
明清时期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为都察院,长官为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这一时期,地方监察加强,监察法规日臻完备,从明代的《宪纲条例》到清代的《钦定台规》,为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行使监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任用主要有三种方式:皇帝直接任命;宰相等大臣举荐,皇帝敕授;御史台长官自辟,皇帝敕授。御史监察的对象上至中央三公、宰相、将军,下至地方州县有品级的官吏。监察官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权力大。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可以监督、纠弹除皇帝与皇太子以外的所有官员,监察内容和范围覆盖了国家政权的所有部门和领域。除弹劾权外,监察官还有审判权、调查权、处置权、荐举权、监军权、监决权等。二是独立性强。监察机构独立,监察官行使职权无须台主或都御史审核同意。这种垂直独立的监察体制,对于整饬吏治,惩治腐败,保障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监察文化是我国优秀政治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强化任用标准,而监察官制度在历史沿革中逐渐清晰,规制也逐渐严密,且涌现出了一批不畏强权、刚正不阿、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均为后人所称赞的监察官。考察我国历史上监察官的由来、选拔任用和考核奖惩等制度规定与运行模式,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当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官队伍。而中国古代对监察官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强化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把好用人关;严格政绩考核,奖优罚劣;严惩职务犯罪,保证监察官员的清明廉洁。虽然监察官制度的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中国传统监察官制度留给我们大量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包括完善监察法律法规建设,监察权力的运行法律化;增强对公权力和政府官员的监督全覆盖及有效性;固定监察与临时监察相互配合以及监察官的互察等,对当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有效实施《监察法》,为监察官法的制度设计进行充分全面的立法准备,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