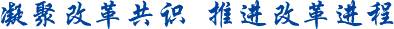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
发稿时间:2018-08-15 12:56:39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朱新力 李芹
[摘 要]行政约谈逐渐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实践表明,约谈方式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置于规制谱系来看,行政约谈应当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并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在制度设计层面,需综合考量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以及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兼顾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未来起到形成性与调整性作用的积极面向,建构约谈程序;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形塑企业的自我反思能力,探索约谈内容。
[关键词]行政约谈;遵从理论;执行金字塔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4-0091-07
[收稿日期]2018-07-10
[作者简介]朱新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一种带有柔性色彩的规制工具,行政约谈日渐为各领域所推崇。从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纷纷出台相应的规范,在具体行政领域内引入约谈方式。行政机关通过约谈进行市场规制和社会治理的实例频见报端,如国家发改委因涨价现象约谈日化企业,北京网信办针对持续传播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约谈新浪微博等等。然而,行政约谈的功能何在,与行政处罚等其他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基础性问题尚不清晰,致使约谈的制度设计也过于粗糙。
尽管约谈已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不过现有研究大多是从行政行为型式化的角度出发,关注约谈行为的性质认定。对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约谈方式而言,将约谈行为予以型式化的努力并无太大助益,急于“对号入座”,难免存在“削足适履”之嫌。鉴于此,本文力图跳出行政行为型式化的传统思维,将行政约谈置于政府规制谱系之中,从整体上考察其功能定位,进而围绕约谈范围、约谈程序与约谈内容,探讨行政约谈的制度建构方向。
一、行政约谈的规则和实践检视
(一)表面的繁荣:行政约谈的兴起与发展
与行政相对人约见谈话的方式最早于2002年出现在税收征管领域。此后,约谈方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不仅仅是价格管理、安全生产、质量监督、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传统规制领域纷纷开始引入约谈方式,面对网络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方兴未艾的新规制领域和规制任务,行政机关也偏好于通过约谈方式实现规制目标。最为典型的当属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2015年4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初步确立约谈制度。事实上,在该规定出台之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曾联合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网易和新浪等年检中违法问题突出、受到大量公众举报的网站,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实践表明,约谈方式日渐成为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领域的主要规制工具。据统计,2015年全国网信系统累计约谈网站820家,[1]2017年仅第三季度被约谈的网站已达798家。[2]
当前行政约谈的制度化过程一般体现为,中央层面各部门颁布规范,引入并鼓励适用行政约谈方式,以此为基础,各地方制定相关规范以实施行政约谈。以食品安全规制领域为例,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0年发布《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率先在国家层面初步确立了约谈制度,随后,其政策法规司探索约谈的制度设计,于2011年发布了《食品药品安全责任约谈办法(征求意见稿)》。2015年修订通过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约谈方式。基于此,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台了专门的约谈规定。
(二)背后的隐忧: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模糊
面对不同的规制领域,迥异的规制任务,缘何行政机关均乐于引入并频繁采用约谈方式来满足规制需要。透过实践探究隐藏于背后的缘由发现,行政机关往往是在规制任务与规制能力存在张力的困境下选取约谈方式,并未真正明晰行政约谈的功能及其在“规制工具箱”中的定位。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其一,行政机关将约谈方式作为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在应对新任务和新挑战时,行政机关的规制能力不足,不仅会陷入法律缺位、规制无据的困境,而且在信息、知识与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此时,行政机关之所以选取约谈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过渡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典型的当属共享经济行业的规制难题,网约车现象完全超出了现行法规范的涵盖范围,兴起之初便引发了交通安全、信息安全、行业竞争等诸多问题,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3]如2015年1月17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安局约谈“滴滴”、“快的”、“优步”、“神州专车”,警醒告诫四家企业严格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合法经营。[4]2015年6月2,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交通执法总队、公安局公交保卫总队等部门约谈滴滴专车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其使用私家车和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5]这一现象揭露出,在进退两难、放管纠结的政策探索期,政府不得不借助约谈方式向网约车平台表明立场和态度。目前野蛮式成长的共享单车行业同样处在一个规则模糊地带。面对无序投放、乱停乱放、押金退还难等乱象,简单粗暴的扣留收缴存在违法之虞,行政机关只能通过约谈方式履行监管职责,甚至在多次约谈未产生良好效果的情况下依旧如此。例如,2018年1月4日,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乱停乱放现象第五次约谈摩拜、ofo两家共享单车企业。[6]针对这种现象,与其急于批评或是担忧约谈的实效性,[7]不如从根本上反思我们期待行政约谈承载何种功能。
其二,行政机关以效率为导向选取约谈方式回应规制任务,忽视约谈方式的价值理性。较之其他方式而言,例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约谈无需受严苛程序的束缚,成本较低,还可以降低事后可能的复议或诉讼风险。这种效率上的优势使得行政机关偏好于通过约谈方式回应棘手的规制任务,特别是经媒体曝光而迅速发酵的公共事件。例如,针对2016年“3·15”晚会曝光“饿了么”网络订餐平台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并审查许可证等问题,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次日上午紧急约谈“饿了么”相关负责人。[8]再如,“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立即就个人信息安全与信息保护问题约谈支付宝、芝麻信用的有关负责人。[9]在行政机关看来,此种情况下的约谈承载着多重目标,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备受公众关注的事件及时作出回应,并非约谈实效。申言之,行政机关通过约谈方式展示其对相关问题的关切,彰显政府的回应性和责任性,存在“象征性执行”之嫌。[10]
当然,本文并非完全否定行政机关在规制任务与规制能力存在某种张力时选取约谈方式的作法,而是重在强调,与其他规制方式一样,行政约谈也并非“万灵丹”。倘若在未准确定位约谈功能的情况下,任由行政机关随意甚至是盲目地进行约谈,不利于约谈制度的具体设计,难以充分发挥约谈的效用,还可能会助长行政机关在规制方式选择上的不理性行为。
二、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
任何一项制度都具备独特的价值与功能,生发于实践过程中的行政约谈更是如此。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是建构约谈制度的基点,影响具体的制度设计,更关乎制度实效。首先有必要厘清的是,在当下政府规制谱系中,行政约谈到底应该以及能够承担怎样的功能?
(一)以遵从理论为基础
威慑(deterrence)与遵从(compliance)是主导行政执法过程的两项基本理论,前者注重惩罚与强制,后者的出发点则是劝服与建议。[11]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偏好于威慑理论,认为企业的守法或违法行为是对成本收益予以理性计算的结果,进而主张通过惩罚确定性和严格程度所彰显的威慑力遏制违法行为。但依旧以威慑理论作为行政约谈的理论基础的话,则会陷入困境。因为在威慑理论主导的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与企业之间处于对抗关系,长此以往,执法过程很可能会演化为“猫捉老鼠”的游戏。[12]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很难获得企业的信任,更遑论彼此通过沟通交流达成任何共识。
遵从理论在假定前提、关注重点与内在逻辑等方面均有别于威慑理论,[13]与行政约谈方式更为契合,能够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指引。首先,遵从理论假定企业最初都是“守法公民”,企业违法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已,其行为动机是多元的。基于此,行政机关应当意识到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更为关注被约谈对象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展开约谈。其次,遵从理论主张将着眼点放在潜在违法行为之上。申言之,在约谈过程中,行政机关重在通过劝服与建议等方式促使企业遵守法律,或是让其认识到一旦违法将会面临严厉惩罚,以此阻止潜在违法行为的发生。最后,遵从理论强调行政机关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对抗转向合作。唯有双方趋向于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在约谈过程中就如何实现规制目标,保障行政实效展开有价值的交流与对话。
(二)以促成守法为目标
经过梳理相关规范文本发现,其中涉及功能定位的表述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具有宣示意味,即概括性规定确立行政约谈制度的目的。如《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约谈办法(试行)》中规定,旨在“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确立约谈制度。另一种是带有工具性色彩。典型表述为,通过约见谈话,了解情况,指出问题,给予告诫,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中指出,通过约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指出问题、责令整改纠正”。不论是宣示性表述,还是带有工具性色彩的功能定位,均不能凸显行政约谈本身的独立价值。尽管在某一具体行政领域内所有规制方式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但不同规制方式的核心目标,或者说着力点,则有所不同。不然,丰富“规制工具箱”的必要性也就无从谈起。
以遵从理论观之,行政约谈的核心目标应定位于促成守法。“促成守法”并不局限于确保企业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激励企业超越最低限度的法律强制性要求,或是在法律已有规定的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目标,或是针对法律未作具体要求的事项展开自我规制。这一点可谓行政约谈与行政处罚等惩罚性方式的根本区别。详言之,行政处罚等惩罚性方式将企业放在了“客体化”的位置上,针对其过去的违法行为追究责任,而行政约谈更多的是面向未来,重视企业在守法过程中的主体性,以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责任。[14]
此外,将行政约谈的核心目标定位于促成守法也契合当下国情。一方面,以促成守法为目标的行政约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或修正当前的行政执法困境。过于依赖以威慑理论为主导的行政执法方式引发了行政机关以罚代管以及企业守法机会主义盛行等乱象,而忽视企业的守法意识及其在特定环境下守法的可能性正是造成当前执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之一。[15]另一方面,以促成守法为目标的行政约谈过程有助于实现政府、企业的角色转变与形塑,符合政府规制体系中引入多中心、多主体合作治理的时代要求。[16]政府在规制竞技场中的角色转变,“典型情形就是从通过命令贯彻实施规则转变成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谈判和协商贯彻实施规则”。[17]与此同时,要想让企业担负起治理主体角色,必须以塑造其责任主体意识和能力为前提。
(三)以惩罚性方式为后盾
任何规制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政府无法再寄希望于某一种规制方式应对纷繁复杂的规制任务,而是要探究多元规制方式之间的优化组合。因而,考量行政约谈与其他方式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明晰行政约谈功能定位的关键。对此,已有规范中虽有涉及,如《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中规定,“责任约谈不影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理”,但现有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被企业俘获,以约谈方式替代本应作出的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理,并没有从整体上考量如何协调行政约谈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其他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最佳规制效果。对此,作为回应性规制理论核心内容的“执行金字塔”提供了一种颇有助益的分析视角。在执行金字塔底端为以遵从理论为基础的执法方式,中间为一般的威慑性执法方式,顶端为惩罚性最强的威慑性执法方式。按照回应性规制理论,行政机关应当优先选取金字塔底部更具协商性的劝服、建议等方式,当这种方式失灵时,行政机关则沿着金字塔逐级向上,施用更具惩罚性的方式。[18]
依执行金字塔的运行规则来看,行政约谈属于一种优先适用的前置性方式。详言之,行政机关应当优先考虑适用行政约谈方式的可能性,倘若决定采取约谈方式,则必须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此种情况下,惩罚性方式从台前退至幕后,经过约谈实现既定规制目标的话,其则处于备而不用状态。之所以要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乃是基于如下考量:一方面,行政机关“手挟大炮才能对约谈对象温柔的讲话(speak softly when they carry big sticks)”,[19]这不仅可以让约谈对象意识到不履行义务的话,将会付出代价,而且可以避免约谈对象在约谈过程中始终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心态,提出法外利益诉求,致使约谈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这样做有助于确保自愿守法企业感到公平,避免其处于一种不利地位。
至于如何实现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还涉及合法性与最佳性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合法性层面,惩罚性方式的设定不得违反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约谈相衔接的惩罚性方式可分为两类:其一,当行政约谈不足以实现既定规制目标时,回归惩罚性方式,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等惩罚性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依据为被约谈对象已有的违法行为,而非约谈情况本身。其二,针对约谈情况本身设定后续的惩罚性方式。目前各领域正在探索通过约谈与信用规制工具相结合的模式,促使行政约谈充分发挥实效。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第8条规定,约谈情况会向社会公开,还将记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日常考核和年检档案。再如根据《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责任约谈办法》的规定,被约谈企业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约谈或未按要求落实整改,情节严重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通报相关部门采取联合惩戒措施。鉴于当前行政约谈相关规范以规范性文件为主,呈现出位阶过低的现实状况,更有必要强调合法性问题,即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惩罚性方式的设定须受依法行政原则和《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的约束。
最佳性层面重在选择性激励,即根据被约谈对象的行为纠正情况,予以区别对待。[20]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第7条中,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未按要求整改,或经综合评估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将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处罚。而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0年颁发的《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所有被约谈对象都将列入重点监管对象,且两年内不得承担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接待任务。这种一刀切的做法难以激励企业积极的作出改进,甚至存在背离约谈制度初衷之嫌。
三、行政约谈的制度建构
上文对行政约谈功能定位的剖析,除了有助于明了行政约谈在整个规制谱系中的定位之外,还为行政约谈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若干指引。如何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建构怎样的约谈程序,谈什么才能使之实现促成守法的目标就是下文需要回应的问题。
(一)约谈范围: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
行政约谈的作用空间并非是完全没有限度的,它能有效应对一些问题,对另一些问题则可能于事无补。因此,合理确定约谈适用范围是确保行政约谈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何时、何种情况可以采取约谈方式,这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等客观事实,还与企业主观层面的守法意愿和守法能力息息相关,需要在确定约谈适用范围时加以综合考量。
从现有规范来看,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的确是影响约谈适用范围的主要因素。但遗憾的是,企业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如何影响约谈范围,相关规范的态度不明,甚至存在矛盾之处。有些规范将严重违法行为作为主要约谈范围,如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第2条、第4条之规定,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情形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可约谈其主要负责人。有些规范则强调在企业存在安全隐患或是涉嫌违法的情况下展开约谈,最早在法律层面确立约谈制度的《食品安全法》当属一例。此外,还有部分规范将潜在违法行为、轻微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一并纳入约谈范围,譬如《江苏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制度(试行)》。从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来看,约谈的启动时点应尽可能向前。申言之,行政约谈范围应当以潜在的或是轻微的违法行为为主。这不止是因为,在现代风险社会,大量风险规制任务要求政府秉持风险预防原则,在没有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就采取措施。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企业存在潜在或轻微违法行为时,行政机关与企业在约谈过程中的协商空间较大。协商空间是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展开沟通交流的基石。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7条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意味着不予行政处罚可以作为一种利益诱导机制,促使被约谈对象积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倘若没有任何协商空间,行政机关很难通过约谈激起企业主动实现规制目标的动力。
除了客观评判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之外,旨在合理确定约谈适用范围,确保行政机关有针对性的展开约谈,更有必要从主观层面考量企业的行为动机,即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根据守法意愿的强弱,可以将企业分为拒不守法者、不情愿的守法者和自愿守法者。[21]有些时候企业作出违法行为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由于欠缺相应的知识与技术抑或对法律法规了解不足等原因造成的,这就涉及到守法能力的问题。[22]综合来看,企业有守法意愿但守法能力不足的情况,最适于纳入约谈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具有一定的守法意愿,虽然可能是不情愿的守法者,但是在行政机关的引导之下,双方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加之约谈过程可以聚焦于企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提供经济、信息支持或是技术指导等方式,尽可能提升企业的守法能力。而针对那些拒不守法者或是守法能力严重不足的企业,约谈方式则并非最优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可以根据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和企业过去的守法记录,评断企业的守法意愿和守法能力,但是变动不居且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依旧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应当更为重视与企业的互动,同时也意味着,不应以一刀切的方式确定约谈适用范围。
(二)约谈程序:兼顾消极面向与积极面向
消极的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是建构行政程序的逻辑起点。但现代行政国家所面临的行政任务已迥异于昔日,迫使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思考超越以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为唯一价值取向的程序观,重新省思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和技术装置。一种积极的程序观逐渐形成,即行政程序并不只是对行政权运行的制约或限制,更不是单纯法律的要求而已,而是同时强调提升行政效能、促进理性形成的积极功能。[23]行政约谈正是在行政任务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程序建构需要兼顾消极面向与积极面向。
消极面向的约谈程序重在控制行政裁量权。不论是约谈前的违法情况判断、约谈对象选择,还是约谈过程之中,抑或约谈后的整改情况评估,行政机关均享有相当程序的裁量空间。旨在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约谈程序至少应当包括如下机制:第一,事前的约谈通知。行政机关在确定实施约谈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约谈事由、依据以及时间、地点等事项。为避免行政机关随意约谈、频繁约谈,告知原则上应当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作出,以详细说明约谈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裁量依据,并给予约谈对象合理的准备时间。第二,事中的意见交流。约谈过程中,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约谈对象的陈述、申辩,并形成多回合的交涉过程。之于行政约谈,陈述意见除了约束行政权之外,还承载着确保行政机关与约谈对象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以及双向互动交流信息的功能。第三,事后的约谈记录。行政机关应当如实记录约谈情况,在约谈结束后,由各方核对确认并签字。载明约谈情况的记录不仅可以避免约谈过程中出现公共利益的妥协和让步,也是优化行政约谈与信用工具、行政处罚等其他规制工具组合使用的关键一环。
与此同时,行政约谈面向未来促成守法目标的实现呼唤积极的程序观。如上所述,行政约谈所应发挥之功能,已不仅是通过事实认定纠正过去的违法行为,更应起到调整性、形成性作用,塑造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能够保障约谈双方充分交流信息、平等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性装置。为此,透过程序机制的架构增进约谈对象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创造合理的沟通与互动模式,强调协商与共识,是日后约谈程序建构与完善的主要方向。鉴于各具体行政领域以及被约谈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现阶段应允许行政机关以协商交流为核心探索程序性装置,“这种自发秩序比之主观设计的程序甚至更具有与实体目标的匹配性和生命力”。[24]
(三)约谈内容:重在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
从相关规范与实践情况观之,尽管当前约谈过程中强调行政机关应当向被约谈对象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听取被约谈对象的陈述,了解相关情况,双方共同分析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其主要基调依旧是惩戒,尚未真正打破关系对立的固有观念。例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解读《食品安全法》第114条时,明确强调约谈是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目的就在于警示和告诫,有一定威慑性,属于“责任告诫”。[25]实践中更为广泛的集体约谈过程通常也是以通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立案处罚情况为主。如陕西省环保厅首次集中公开约谈企业,即重在通报29家污染企业超标排放的具体情况。[26]
如前文所述,与威慑性方式不同,行政约谈不应过分凸显行政机关与被约谈对象之间的对抗,因为这会严重妨碍约谈制度功能的发挥。在约谈过程中,各方要带有诚意进行对话,具体体现为各方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具有建设性的沟通交流。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被约谈企业才有可能敞开心扉,行政机关才可以充分掌握被约谈企业的行为动机等具体情况,进而有的放矢的作出回应与引导。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还有助于行政机关借此机会了解被约谈对象所属行业面临的问题,以便日后制定更为合理的规制方案。
最佳的约谈效果是,经由沟通交流,行政机关不仅让企业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还要塑造企业的守法意识与责任意识,引导企业由消极抵抗变为积极守法,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守法水平。这意味着约谈绝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闲聊。事实上,约谈对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谈判以及专业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需要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对此,心理学领域内成熟的动机式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具有启发性,可资借鉴。动机式访谈的逻辑在于帮助人们突破关于想要改变却不愿改变的矛盾心态,其精髓在于激活人们自身关于改变的动机和资源。将动机式访谈法应用于行政约谈过程,为行政机关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或具体技巧:首先,约谈要求行政机关与约谈对象之间真诚的协作。其次,行政机关应当重点听取约谈对象的陈述,探究其未充分履行法律义务和承诺履行法律义务的矛盾状态。最后,行政机关聚焦于约谈对象所作陈述中涉及承诺的内容,由此引导并强化约谈对象作出预期改变的内在动力。[27]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约谈过程中的角色不能停留在直接告诉被约谈对象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唤醒并强化被约谈对象遵守法律法规的内在动力,形塑被约谈对象的自我反思能力。
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机关与约谈对象之间真诚地沟通交流,不仅对双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赖于互相信任关系的建立,但还是要认识到,理想的约谈过程看起来像是跳舞而不是摔跤,行政机关与约谈对象向着同一个目标移动,而不是一种对抗和牵制对手的过程。
四、结 语
本文尝试从政府规制谱系出发,剖析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探讨约谈的制度建构方向。在政府规制谱系中,行政约谈属于一种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的规制方式,应当淡化行政机关与被约谈对象之间的对抗色彩,注重以诚意为基础的协商对话。除了行政约谈制度本身的合理设计之外,行政约谈尚需要与行政处罚等威慑性方式相配合,才足以保障行政约谈的实效性。此外,当前行政约谈制度的运用还面临着若干挑战。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致使行政机关与被约谈对象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在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尚未摆脱投机性营利困局的背景下,企业的守法意愿和守法能力不免令人堪忧,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限制约谈制度功能的发挥。凡此种种,有待于日后更为务实、更加细致的实践探索,反过来为相关规制理论的修正与发展提供素材。
[参考文献]
[1]全国网信系统执法“亮剑”820多家违法违规网站被约[EB/OL]. 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16-02/26/c_1118173992.htm,2017-12-17.
[2]重拳出击形成有力震慑 ——三季度全国网信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EB/OL]. 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17-10/27/c_1121868206.htm,2017-12-17.
[3]金自宁. 直面我国网络约租车的合法性问题[J]. 宏观质量研究,2015 (4):100-108.
[4]戴璐岭. 成都市交委、市公安局约谈“快的打车”等4家专车公司[EB/OL]. http://news.163.com/15/0117/18/AG6CSUA700014AEE. html,2017-12-17.
[5]郭超. 北京交通委约谈滴滴专车、快车违法[EB/OL]. http://www.bjnews.com.cn/ feature/2015/06/03/365772.html,2017-12-18.
[6]李升. 兰州交警教育部门联合约谈共享单车企[N]. 兰州晨报,2018-01-05 (A05).
[7]马讯,杨海坤. 行政约谈实效性的保障机制建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1):79-87.
[8]市食药监局约谈“饿了么” 督促落实平台主体责任[EB/OL]. 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www.shfda.gov.cn/gb/node2/yjj/n5100/u1ai48506.html,2017- 12-17.
[9]张洋. 国家网信办约谈“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当事企业[N]. 人民日报,2018-01-11 (11).
[10]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M].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
[11][21]Neil Gunningham.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Strategies[A]. Martin Cave,Robert Baldwin and Martin Lodg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C]. 2010:120,99-100.
[12]Eugene Bardach,Robert A. Kagan. 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M].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20.
[13]Albert J. Reiss. Selecting Strategies of Social Control over Organizational Life[A]. Keith Hawkins and John M. Thomas (eds.). Enforcing Regulation[C]. Boston:Kluwer-Nijhoff,1984:24-25.
[14]John Braithwaite. The Essence of Responsive Regulation[J]. U.B.C. L. Rev.,2011(44):510,496-497.
[15]何香柏. 我国威慑型环境执法困境的破解[J]. 法商研究,2016 (4):24-34.
[16]宋华琳. 论政府规制中的合作治理[J]. 政治与法律,2016 (8):14-23.
[17][英]哈洛等. 法律与行政(上)[M]. 杨伟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77.
[18][19]Ian Ayres,John Braithwaite. 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35-36,19.
[20][美]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
[22]Robert A. Kagan,John T. Scholz. The Criminology of the Corporation and Regulatory Enforcement Styles[A]. Keith Hawkins and John M. Thomas (eds.). Enforcing Regulation[C]. Boston:Kluwer-Nijhoff,1984:80.
[23]叶俊荣. 面对行政程序法:转型台湾的程序建制[M]. 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290.
[24]朱新力,唐明良. 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基本图谱——“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结构的展开路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35.
[2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299.
[26]陕西省首次集中公开约谈污染企业[EB/OL]. http://www.sxdaily.com.cn/n/ 2015/0408/c266-5661711.html,2017-12-17.
[27]崔俊杰.我国当代行政法治变迁的特色、反思与前瞻[J].行政法学研究,2016(1):9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