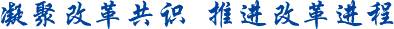社会“变狠”是今天严峻的问题
发稿时间:2016-09-29 10:08:44 来源:南风窗 作者:于建嵘 赵义
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解体之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情况正在起变化。
这些年来,诸如“社会溃败”、“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词语,一直被用来描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社会在“变狠”。而且,它是内嵌于社会结构里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说清楚,捕捉它的发生逻辑,警示它能带来什么。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狠化”状态作出诊断。
状态
《南风窗》:一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难免就会说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会让人情绪不太稳定,比如贫富的悬殊,二代的世袭。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这是中国社会向一个现在并不预知的未来演化时,处于某种阶段的特征。
可是仅仅是用这些现象来概括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难以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在今天的特征。我们毕竟感觉到,贫富悬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整个社会的状况,前两年和过去,今年和前两年并不一样,有最新的变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心态的影响,也许更为严重。您觉得社会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于建嵘:你说的没错。我们应对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再仅仅用“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词语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你刚才所说的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到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南风窗》:就是说,社会在变狠。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的时候,老百姓也变狠。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终于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化”。
于建嵘:对!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现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南风窗》:当我们发现“变狠”渗透于所有阶层,以及从制度到行为到心态时,似乎要对在社会演化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作出一个判断。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细致的量化的指标,这估计也难以做到。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原因
《南风窗》: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变狠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主要还是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利益失衡,这个好理解,还能有一些补偿机制,包括心理层面也有。规则失效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规则失效的话,我们会退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暴力法则就应运而生。暴力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因,只不过依赖规则的进化,暴力“潜伏”了下来。一旦规则失效,它就会开始复活。
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
人物介绍

于建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